在你的成都,我改變瞭口味
1
見陳廣智之前我很緊張,在寢室裡拿著夾板一遍又一遍地燙著劉海兒,塗瞭手指甲,還用拙劣的技術化瞭妝。衣服換瞭好幾套,站在鏡子前反復照,不知道怎樣才能讓我看上去更漂亮。
在這之前,我和陳廣智剛在QQ上結束瞭50個小時沒日沒夜的聊天。而3天前,我們還是在大學校園裡碰面都不認識的陌生校友。
陳廣智在女生寢室樓下等我,我們沒看過彼此的照片,但當我跨出寢室大門,看到他的第一眼時,內心就有個聲音告訴我:就是他瞭。幾分鐘後,我和他當場決定:在一起。
我們倆這個默契的共識達成於2009年的5月一個黢黑的夜晚,可好多年後想起來,還覺得是個艷陽天。後來,陳廣智從他的視角,還原瞭第一次見到我時的場景——
“就記得那晚約你去燒烤攤吃宵夜,你一串接一串地吃,頭都沒抬一下,還一個勁兒地說‘好吃,好吃’,我心想,你是不是沒吃晚飯哦,有那麼餓嗎?”
我抑住怒火,微笑著幫他回憶我當時精致的妝容,他認真思考一番,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,但隨即補瞭一句:“想起來瞭!吃燒烤的時候,你嘴唇上的口紅都花瞭。不過看你吃得那麼香,我當時都不忍心提醒你瞭。”
接著,他順口反問我,為何會輕易地接受一個認識不過3天的人,我抽絲剝繭,發現我對他動心的點,竟是見面前一天的深夜,我們聊天時他突然打瞭一句:“你稍等下,我有點餓瞭,出去買個燒烤。”
當時我的寢室早已鎖門熄燈,一個“燒烤”,把我饞得百爪撓心。我躺在寢室的二層床上,猛咽瞭幾下口水,腳蹬在天花板上,忽然有個念頭在我腦袋裡瘋狂冒泡:他要是我男朋友就好瞭,至少能半夜幫我打包一份燒烤。
陳廣智聽完我的回答後哭笑不得:“那你怎麼不去找後門賣燒烤的那個小哥?近水樓臺先得月,包你吃個夠。而且,每次看你和他聊天聊得也挺嗨,你咋不和他談戀愛呢?”
我想瞭下,認真地回答他:“那小哥太愛吃瞭,邊烤邊吃,我怕搶不過他。”
陳廣智敲瞭一下我的腦袋,表示從來沒見過這麼好吃的人,“還是個女生!”他又補瞭一句。
對於我的這張“好吃嘴”,那時候的陳廣智並不能和我產生共鳴。他來自江蘇徐州,那是座歷史底蘊深厚的城市,自古以來就是兵傢必爭之地,在那裡長大的他,並不能對成都的安逸感同身受。
2
陳廣智與成都的淵源,要追溯到2007年。
那年夏天,他趴在中國地圖上,手指在“哈爾濱”和“海南”之間來回遊走,挑選未來四年生活學習的大學。但與其說是選大學,不如說是選城市:首先要離傢遠,不能一腳油門就被傢長探望;其次,城市要宜居。
忽然,陳廣智的腦海裡蹦出瞭“少不入川”四個字,他認為這是對一個城市的褒獎,便順手把四川也納入選擇范圍。
那時,手機還不夠智能,不能支持陳廣智隨意放大電子地圖、把他用10分鐘就決定好要去的城市看個透。他也萬萬沒想到,自己隨意填寫的第三志願最終會將他錄取。不僅如此,在那座陌生的城市,還會遇到一個我,徹底改變瞭他以後的生活軌跡。
2007年8月開學報道前一天,坐瞭30多個小時的火車,陳廣智和他父親輾轉來到學校時,倆人已饑腸轆轆。
學校後門有條小吃街,白天僅有連排的商鋪營業。街邊的臺階上佈滿瞭成片的油漬,暗示著此地別樣豐富的夜生活。
落日餘暉中,路邊攤紛紛開張,學生們蜂擁出巢,整條街瞬間換瞭風格。小攤一傢挨著一傢,燈火通明,亮度逼人,霸占瞭整條街巷。有老板操著四川話,中氣十足的吆喝聲;有三五成群的學生,把牛皮吹上天的聲音;有食材在熱油上煎炸的“嗞嗞”聲;還有急躁的汽車喇叭聲,司機們盼著能在密密麻麻的路邊攤中擠出一條小道。
打小陳廣智便跟著做生意的父親一同混跡在各大飯局上,父子倆一致認為路邊攤是“臟、亂、差”的代名詞,兩個大老爺們兒窩在路邊吃小攤兒,實在不體面。於是兩人眉頭緊鎖,快速地通過小吃一條街,拐進一傢稍顯高檔的川菜館。
聽說川菜以“辣”出名,兩人商量著,怕初到成都腸胃不適應,便順著菜單想找些清淡的。兩人同時鎖定瞭“水煮肉片”這道菜名——“水煮的,一定清淡又養生。”
當老板端上來那盆蓋著厚厚一層花椒和辣椒、在滾燙的油中爆發出“呲啦呲啦”聲音的肉片時,從江蘇來的父子倆不由一愣,果不其然,嘗瞭一口便被嗆出眼淚。
陳廣智猛灌瞭幾口白開水,心裡更是一通抱怨:自己選的城市一點都不“宜居”,連一個“白水煮菜”都那麼辣。隻是礙於面子,陳廣智不願向父親承認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。
隻是後來,陳廣智告訴我,吃完那頓飯,他就當場決定:畢業後一定不能留在成都,“這個城市實在是太不對胃口瞭”。
3
我和陳廣智確立戀愛關系後的第一頓飯,就上演瞭一場關於吃的“博弈”。
星期六的早晨,他如約到寢室樓下接我。這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,雖然在QQ上24小時不間斷地廢話連篇,可面對面還是不免有些尷尬。
陳廣智是個1米86的大高個兒,他在我的前面三步並作兩步地走,我跟在後面都快要跑斷氣瞭,也沒好意思開口讓他等等我。直到他無意間回過頭,見我在喘著粗氣,就用蹩腳的四川話問:“你咋子瞭?那麼累呢?要不要坐下來吃口東西緩緩?”
我這才意識到,自己對他的聲音非常陌生,不標準的四川話從他嘴裡冒出來,聽上去很滑稽。“沒關系,你可以和我說普通話。”剛說完就發現自己把話題帶偏瞭,趕緊補瞭一句:“好,那坐下來吃點東西吧。”
陳廣智提出去學校附近的一傢西餐廳,那是學生界的“高規格”餐廳,招待“貴賓”的首選,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對我的重視。我聽瞭後卻像個泄瞭氣的皮球,但由於兩人還不熟,我並沒有提出異議。我點瞭一份最便宜的牛排,放在口中如同嚼蠟,吃瞭一塊便放下刀具。
那天傍晚,陳廣智讓我決定晚上吃什麼。我抬起頭,遞上一個善解人意的微笑:“不用不用,我吃什麼都可以。”腳步子卻一個勁兒地往學校後門的小吃街挪,一邊走,一邊用餘光快速地掃過周圍的路邊攤,腦袋裡瘋狂盤算著要臨幸哪一傢才能安撫我的胃。
最後,我選瞭一傢窩在墻角邊上的路邊攤吃冒菜。落座時,我明顯看到陳廣智環顧瞭下四周,露出瞭猶豫的神情。可是,此時冒菜的香辣味已然傳到瞭我的鼻腔裡,饞得我顧不瞭那麼多瞭,便假裝沒看到。
冒菜是四川特色小吃,把土豆片、藕片、紅苕粉、鴨血、豆芽等素菜,裝在用竹子編成的簍裡,老板借助腕力,將竹簍放入用火鍋底料和高湯熬制而成的湯底裡“冒”。當菜品滲入湯汁後打撈出鍋,放入碗中,再配上小米辣、辣椒油、花椒等佐料,舀上一勺湯底,把香辣提升到極致。
陳廣智問我為什麼喜歡吃冒菜:“這樣的小攤兒很不衛生。”
“其實我愛吃火鍋,可是一個人去吃火鍋太尷尬瞭,最多吃一兩個菜就飽瞭,冒菜多好,十多種菜全有,隨時都可以感受私人火鍋般的頂級待遇。”我說完,陳廣智笑著看著我,沒有接話,我又補瞭一句,“你聽過這麼一句話麼,‘冒菜是一個人的火鍋,火鍋是一群人的冒菜。’所以啊,其實火鍋冒菜都一樣,就看是自己吃,還是和別人一起吃。”
“你要是愛吃火鍋,我以後就經常陪你去吃。當然啦,我吃白味湯底。我聽說你們四川人覺得吃白味是對火鍋的侮辱,你可別嫌棄我哈。至少我陪你,以後都就不用吃‘一個人的火鍋’瞭。”陳廣智撓著頭,露出害羞的表情。
對我來說,這是陳廣智對我說的第一句情話。
我夾起一片藕送進嘴裡,在牙齒的咬合下,滲出一絲絲的甜味,配著香辣傳到胃裡,胸膛暖呼呼的。原來和喜歡的人一起吃飯,竟然可以這麼開心。
“2009年5月19日,我和陳廣智一起吃的冒菜,比生命中任何一次都好吃。”我在那天的日記裡這麼寫道。
4
陳廣智在和我一起吃瞭約400頓飯之後,成功被洗腦,儼然成為我攻克美食道路上的幫兇。
剛在一起的那一年,團購網站還是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新興產業。那時候每天最開心的事,就是一口氣把收藏的20多傢美食團購網全部開啟,寢室網絡不佳,我會歸正瞭鼠標和鍵盤,坐直身板兒等待網頁緩沖出來。然後挨傢篩選,看圖片和口碑。但凡有評論表示這傢食物好吃,我一定會拉著陳廣智去嘗一嘗。
父親從小對陳廣智的教育就是:凡事不要拖拉,時間要用在節點上。因此,陳廣智總是對我趕公交車,穿梭在成都各大街小巷尋找美食的行為嗤之以鼻。
而我從小路癡,在生活瞭20多年的城市也時常會迷路。憑借著這個借口,陳廣智隻能妥協。他負責找路,我負責吃,這成瞭我們異於常人的默契。
我挖地三尺才找到的美食,經常需要排隊。陳廣智對此非常不理解:“吃飯不就是填飽肚子的事兒嗎?在我傢那邊,沒人會把時間浪費在排隊吃飯這件事兒上。能吃就進,不能吃就走。這些人,真是閑的。”
“吃飯是一種享受,排隊是對美食的尊重,這是最有儀式感的事!”我據理力爭。
“那你咋不戴上紅領巾去吃飯?那樣更有儀式感。”我時常被陳廣智懟得啞口無言,但往往是他一邊嫌棄我,一邊陪我嘗試那些“有儀式感的”的美食。
那段時間我幾乎嘗遍瞭成都所有的“網紅火鍋”。我跟陳廣智說我小時候經常問父母為啥不開火鍋店,陳廣智給瞭我一個答案:“要是開瞭火鍋店,還不被你天天吃給吃垮瞭。”
有次,他陪我排隊時,拉著同在排隊的人,在火鍋店門口玩起瞭鬥地主。我嘲笑他:“你終究還是成瞭你曾經最討厭的那類人。”他狡黠一笑,回敬道:“別人是近朱者赤,和你一起,是近豬者豬。”
此話也不無道理,我從小就無辣不歡,火鍋一定不能配油碟,那樣會破壞火鍋底料的厚重感,原湯加幹辣椒面才是完美搭配。要是能再舀上一勺小米辣,鮮辣與麻辣雙重刺激,更是會調動起全身的細胞。陳廣智在我的帶領下,可以駕馭任意一種四川特色的辣。曾經把他傷害得很深的“水煮肉片”,後來對於他來說隻能算作辣味鏈上的最底端。
5
成都真正的美食,大多數是路邊攤,隱藏在小巷中。
我時常逗陳廣智:“這些藏在卡卡角角(四川話,角落,音kakaguoguo)的路邊攤,你看美食攻略是完全找不到的,隻有我這種本地人才能搜刮得出來。我忽然發現你真是居心叵測,你找我,就是為瞭讓我帶你去吃這些正宗的路邊攤兒吧?”
陳廣智不屑一顧:“你以為我和你一樣,就那點出息啊?別人找對象是看車看房看戶口,到你這兒,就為一口吃的瞭。”
張奶奶的攤兒就是我們的老窩之一。這裡最開始賣的是狼牙土豆,業務壯大之後,又加瞭涼面、冰粉、燒烤、冒菜等。
我和陳廣智時常熟練地搬來小桌,放在墻角,窩坐在跟前。周圍是鬧哄哄的中學生,匆匆買瞭就走,他們有時會多看我們幾眼,陳廣智窩在一群穿著統一校服的半大孩子堆裡,的確很突兀。
前幾年,張奶奶在擺攤的時候出過一場車禍。一個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司機將車輪碾上瞭路邊的臺階,撞翻瞭攤位。正在削土豆皮的張奶奶來不及躲避,頭部受傷,以至於現在的記憶力很差。
雖然我們多次光顧過張奶奶的路邊攤,但她每次見我還是會致歉,表示忘記瞭我的口味。陳廣智則習慣性地在一旁提醒:“張奶奶,幫我女朋友多放點小米辣,不要客氣,直接給她拌成‘超級變態辣’,土豆剛過心就撈,一定要脆。不要味精,謝謝。”
每次陳廣智挺不好意思地說完這一長串的口味備註,張奶奶就笑盈盈地表示,下次一定記得。盡管如此,幾年的時間裡,這情景總是循環上演。
張奶奶拌的狼牙土豆(作者供圖)
2011年,陳廣智大四的那個寒假,我跟他回瞭次徐州。那裡有成都少見的大雪,蓋住馬路。牙膏凍得需要用熱水燙一下,才能擠出來。戴隱形眼鏡也成為我每日的一項挑戰。
陳廣智的傢鄉飲食口味清淡,幾乎沒有辛辣。他們愛吃羊肉,幾乎每頓都不落。而在成都,隻有“冬至”那一天會喝羊肉湯,我因為吃不慣羊肉的膻味,每次都會避開。我用真空袋打包的鹵兔頭,也沒人願意和我分享——大傢認為吃兔子是件很殘忍的事。
陳廣智怕我吃不慣,就提出帶我去掃蕩我最愛的路邊攤。
陳廣智高中門口也有一條小吃街,他熟絡地和老板們打著招呼,並熱情地向大傢介紹“這是我的女朋友”。老板們聽說我是個“川妹子”,主動提出要在“蛙魚”裡加辣椒。
“蛙魚”是徐州的一種形同小魚的面食,口感爽滑,自帶酸甜口味。我嘗瞭一口,並沒有吃出期待的辣味。我在心裡拼命對自己暗示:這是陳廣智喜歡的傢鄉菜,我要喜歡,以後要適應的還有很多。
晚上,我一個人溜到小區門口,光顧瞭一傢我白天瞥見的名為“四川麻辣燙”的店鋪。老板娘是成都人,嫁給瞭一個徐州人,從此在這生活。她曾在成都開過一傢冒菜館,我吃第一口時,就嘗到瞭自己熟悉的味道,頓時胃口大開。
隻是吃著吃著,我忽然對自己很失望,停下瞭筷子。或許自己和“四川麻辣燙”一樣,於這座城市而言,都是多餘的。
我吃到一半,陳廣智找到瞭我。老板娘聽說我也是成都人,絮絮叨叨講瞭很多:她來徐州後,什麼都吃不慣,才想著把自己在成都的事業帶到這邊來,做個念想:“有這個鋪子,我才沒那麼想傢。”
那頓飯,我們都沒有說話。
陳廣智的父親希望兒子能回傢發展,子承父業,在這個理由背後,還藏著那句中年男人難以開口的:兒子,爸想你瞭。陳廣智也褪去瞭四年前的那份浮躁,那顆四海為傢的心,早已被認定為是一種不負責任。
他不願把背井離鄉的包袱丟給我,經過幾個月的掙紮,在畢業之際,決定自己獨自回傢。
回傢就回傢吧,沒事,就這樣吧,能有什麼事。我想。
6
雖然自認為沒什麼,但身體還是誠實地出現瞭狀況。
自陳廣智回傢的那一刻,我仿佛失去瞭味覺,吃什麼都覺得毫無滋味。在他回傢後的第21天,我的兩個閨蜜搞瞭場“尋味之旅”,想拖我離開這場失戀的暴風雨。
兩個姑娘拉著我來到張奶奶的路邊攤,張奶奶察覺到我的反常,把狼牙土豆端給我時,順勢坐在瞭我旁邊的小凳子上,用身上的圍兜擦瞭擦手:“丫頭,你那個絕世好男朋友咋沒來?”
我有些詫異,張奶奶竟然用瞭“絕世好男朋友”這樣新潮的詞,而更讓我詫異的是,記不得我口味的她,竟然記得陳廣智。
“我們分手啦,張奶奶,他回他自己的城市啦。”我故作輕松地回答。
“咋個分開瞭?他對你那麼好。為啥子喃?”張奶奶是個急性子,和我傢院壩裡的老奶奶們一樣,熱情、單純、又八卦。她從圍兜裡抓出一大把零錢,遞給她女兒,準備專心聽我講述。
被一個不算熟悉的長輩問到感情問題,我有些不知道該如何接話。
張奶奶握住我的手說道:
“他真是個絕世好男朋友,每次來給你打包狼牙土豆時,我小女兒都會這樣念叨一遍。
“張奶奶我老瞭,手腳也不麻利,我都讓小女兒幫我提前炸好三大鍋的土豆,再拌好三種口味。這樣來一人,舀一碗,夠賣大半天勒。每次你男朋友來,都喊我單獨給你炸一小碗,說那樣才是脆土豆,才能拌出你喜歡的口味。
“有時候趕上學生放學的點兒,我們啊,根本莫得空單獨弄,他有時還親自切蔥,個人搗蒜,等我們忙過這陣,再喊我單獨給你拌。有時候,我看他那麼大高個子,站在墻角切土豆,我都不忍心。他還傻笑,說女朋友好養活,吃個土豆就笑瞇瞭。
“我傢開瞭有10年瞭,啥子顧客都見得多咯。很多小年輕談朋友,女娃娃喜歡吃我們這種攤攤兒,男娃娃卻看不上。有的還躲多遠,覺得掉價。也是,哪個小男娃娃不在乎點兒面子喃?”
我無法接話。
我低著頭,用竹簽插瞭好幾坨狼牙土豆,一口氣吞下。土豆炸軟瞭,在嘴裡混成一大團糊糊,吞不下去,吐不出來,卡在喉嚨裡,眼淚噎瞭出來。
7
兩年的接觸,我怎麼會不知道陳廣智是個多麼溫暖的人呢。
大三的時候,陳廣智吃瞭一個月的方便面,存錢給我買瞭一條裙子,699元,是我一個月的生活費。我舍不得,大發雷霆,讓他立馬去退。他沒料到我如此反應,隻得依著我。
陳廣智站在銷售阿姨面前,表示要退貨。店員瞬間提高音量,來回擺手,表示“衣服出售概不退貨”,僵持不下,最後把陳廣智晾在瞭那裡。他提著袋子,站在女裝店鋪裡,低著頭,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。最終,店員嫌棄他妨礙生意,同意退貨。
陳廣智捏著那699元,遠遠地向我招手,笑著跑到跟前。我的歉意還未表達,他先向我道歉:自己不該拿著父母給的生活費送我禮物,他要做的是畢業後努力工作,靠自己的雙手,讓我過上更好的生活。
“他不是說畢業後要努力工作,讓我過得更好嗎?他現在又跑到哪裡去瞭……”
張奶奶沒有回答我。或許她答瞭,我沒有聽見。我的眼淚刷刷地流,四周死一般寂靜。
陳廣智回傢後,並沒有忙著找工作,而是天天窩在傢裡打遊戲、睡覺、和老同學去籃球場打球。打完籃球,老同學們常常會約著在一起去吃宵夜,“戒瞭。”他一次都沒有去過。
他不僅戒瞭宵夜,連一日三餐也是能省則省。
一個月的時間,陳廣智瘦瞭15斤。所以當他頂著一臉胡渣子,再次跨入“四川麻辣燙”時,老板娘竟沒有認出他。
他打包瞭一份麻辣燙,還讓老板娘用小口袋額外裝瞭好幾勺辣椒面,“怎麼吃都不好吃,越看那個辣椒面,就越像紅磚末兒,倒胃口”。
那段時間,陳廣智學會瞭喝酒。仿佛自己的失眠可以借助酒精得以緩解。但喝瞭酒,還是睡不著。一次,陳廣智半夜起床,切瞭一塊固體火鍋底料,丟在鍋裡,和方便面一起煮。火鍋底料是前幾天在網上買的,是成都一傢隨處可見的火鍋連鎖店生產的袋裝底料。
拌著濃厚的辣味,他連吃瞭幾口。不知道是吃得太急,還是餓太久瞭,胃裡一陣翻滾,沖進廁所吐瞭起來。
陳廣智按下馬桶上的按鈕,“嘩——”,他忽然覺得一身輕松,好像有一盆水,“嘩”地一聲把他從頭淋到腳。
他突然想明白瞭,做瞭一個決定。
8
2011年8月底,陳廣智又回到瞭我的城市,像是過瞭一個普通的暑假,回成都來報道瞭。
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:“我回傢後竟然吃不慣傢鄉菜瞭,兩個月沒吃辣椒,憋得臉上冒起瞭痘痘。我每天都在想成都的美食。”沒等我開口,又說瞭句,“更想你。”
“回傢後,我什麼都吃不下去。每天都在擔心,擔心你想吃東西瞭,沒有人給你買,怕你餓著,怕沒有人照顧你……現在看你也沒餓瘦,我還挺失望的,我是不是想多瞭?”陳廣智認真地問我。
我“噗呲”一下笑出聲,笑著笑著,又撅著嘴開始流眼淚。我沒有回商標登記查詢台中|商標登記費用台中答他,隻想讓他好好抱抱我。我個子不高,臉正好貼在他的胸膛上,聽著心臟在我耳邊怦怦跳動。
從那時起,我恢復瞭味覺。
陳廣智兌現瞭他的承諾,在成都找瞭一份工作,工作之餘我們繼續嘗試各路美食,成都遍地都有我們的腳印。畢業多年後,我們仍時常回到大學,隻為回味那些年被我們寵幸的路邊攤。
泡椒魚米線的老板,還是會特意為我挑一個魚泡;有傢冒菜館,明明有著自己的招牌,由於門口掛著一副對聯——“山不在高有仙則名,店不在小有辣則靈”,被我們倆“山不在高”地叫瞭好幾年;還有最愛的一傢火鍋店,春去秋來,我們習慣性地坐在靠窗的位置,翹首等待原湯在鐵鍋裡冒出的一個泡兒。第一筷子永遠是夾千層肚,倒計時15秒起鍋,陳廣智燙得那份會第一時間夾到我的碗裡。
後來,我們還把路邊攤文化延伸到瞭其他地方,我們一同去瞭泰國,窩在大排檔前,老板比劃著為我們推薦瞭一個泰式湯鍋。當高聳的銅鍋端上桌,正好擋住瞭我面前的陳廣智,我和陳廣智同時搬著小凳子挪向瞭同一個方位,肩並著肩,擠在一起開吃。
對面街上人來人往,被太陽烤得發燙的地面,騰起熱浪,撲進眼睛裡,暖暖的。
9
後來,我和陳廣智再也無法盡情流連於路邊攤瞭——我們的小小陳出生瞭。
小朋友是個十足的搗蛋大王,初為父母的我們,手忙腳亂,很難安份地吃完一頓飯。每次寶寶在飯桌前抗議,陳廣智就會假裝嚴肅地說:“你別鬧媽媽,有種沖我來啊,小子!”
寶寶咿呀學語,最先清晰蹦出的兩個字,除瞭“台中註冊商標推薦|台中註冊商標事務所推薦媽媽”、“爸爸”,還有一句“好吃”——他算是徹底繼承瞭我的好吃嘴。
如今,陳廣智時常需要出差,我舉著手機和他視頻,叫兒子過來看爸爸。小傢夥傲嬌得很,任陳廣智怎麼喊他,他都自顧自地玩著手邊的玩具。隻有一個辦法能瞬間抓住他的註意力,我說:“小子,快來看爸爸正在吃什麼呢。”
陳廣智會配合著咂嘴:“嗯,好吃!真好吃!”
寶寶立馬奔瞭過來,伸個腦袋在手機面前,“爸爸,你在吃啥好吃的呀。你快回來吧,我想你瞭,我好乖,爸爸給我買好吃的回來吧。”
等小小陳長大些後,陳廣智會領著兒子,和我一起光顧張奶奶傢的路邊攤。張奶奶的曾孫子很喜歡和小小陳一同玩耍,有時候,張奶奶還會送一碗新鮮出爐的白味狼牙土豆給兒子解饞。
上個月,在吃狼牙土豆的時候,兒子摟著我的脖子,問陳廣智:“爸爸,我和老媽都是好吃嘴,你愛我們嗎?”
“當然,我好愛你們。”
本文系網易獨傢約稿,享有獨傢版權授權,任何第三方不得轉載,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。
“人間有味”長期征稿,歡迎大傢將自己與食物有關的文字、圖片稿件投遞至人間郵箱:thelivings@163.vip.com 我們在這裡等你。
題圖:golo
插圖:作者供圖
2013年,我市和上級地級市的“市長熱線”聯合辦公,增加瞭網絡投訴平臺,整合成為行政專線,業務擴大後,需要再招一批工作人員,我便從9月開始,到那裡工作瞭一年。
市政府的行政辦公區位於新修建的紫薇大道上,行政專線占用瞭一樓東頭的3個辦公室,最大的有一個教室大小,是“接辦區”,對面的兩間小辦公室分別是“轉辦區”和“回訪區”。接待我的是負責接辦區的王主任,30多歲,中等個子,面相和氣——後來我才知道,凡在這裡待的時間長一些,能負點責的,都會被冠以“主任”的稱呼。
行政專線由市政府和市紀委雙重領導,部門屬性不明,成員構成也頗為復雜。這裡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是李主任,他本身是市紀委督察室的主任,平時工作重心在紀委,很少來這裡,所以日常工作便由王主任和張主任負責。王主任正式編制在畜牧局,借調來此,是當初專線成立時的兩大元老之一;李主任則是從鄉鎮借調來的教師,負責轉辦和回訪,定期向市政府進行情況匯總。其餘十幾個工作人員,大部分都是從學校抽調來的老師,也有小部分像我這樣,屬於勞務派遣,由勞務公司統一發放工資。
所以說,這是一個沒有編制且不需要發工資的正式單位。
作為菜鳥,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接辦區接電話。王主任說,當初專線成立時,他的工作也是從接電話開始的。推開接辦區辦公室的門,裡面有4個30多歲的婦女。王主任簡單介紹瞭下,又吩咐一個叫程燕的大姐帶我幾天,說罷轉身出去瞭。我有些不好意思,拘謹地坐在王主任指定的位置上。
程燕看上去是個開朗的人,她告訴我:“桌上的電話是和電腦相連的,每個電話接進來,都會在電腦上顯示出來電的基本信息,當然,電腦上也會留下相關記錄。”她又特別提醒我:“每一次通話都會被錄音,所以說話時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措辭,不要給人留下把柄,更要避免遭到投訴。”
正在這時,鈴聲響瞭。她示意我將帶著話筒的耳機戴好,然後按下瞭接聽鍵。
就這樣,沒有崗前培訓,沒有工作經驗,我的接話員生涯開始瞭。
電話這頭沒有市長
電話對面是一個男人的聲音。他是一個賣菜的小販,當時正是開學季,適齡的孩子已經開始上課,而他的孩子還沒有學可上。
按照教體局的規定,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需要在戶口所在地報名上學。他和孩子的戶口還在鄉下老傢,不在市裡,所以隻能回鄉下上學。
我把教體局的規定向他解釋瞭,可顯然他打電話過來不是聽我解釋的:
“你看,我們兩口子每天凌晨4點多就得去市場批發,在街上轉悠一天才能賣完,全傢人都得靠這個吃飯。我們要是把孩子送回老傢,那就得有一個人回去看孩子,生意就做不成,我們還怎麼生活……”
“我聽說市裡的學校是允許借讀的,你幫我問問,到底怎麼個借讀法兒。隻要孩子能上成學,出錢我們也願意。唉,我們就是個賣菜的,城裡一個朋友也沒有,傢裡也沒有有本事的親戚。眼看著別的小孩都去上學瞭,孩子在傢裡鬧個不停,求求你們給我想想辦法吧!”
我仔細看著教體局的文件,一行行文字清晰冷靜——“隻有外地務工人員的子女可以憑借相關證明,在市區學校借讀”。
男人憤憤不平:“外地人都可以在城裡上學,我們本地的鄉下人卻不能,這是什麼狗屁規定!你們就不能讓市長管管嗎?”
“讓市長管管”這句話在以後的無數個電話中頻繁出現,很多打來電話的人都以為這頭就坐著市長,可以滿足他們各種各樣的需求。可事實上,在我工作的一年裡,市長隻有在陪同上級領導考察行政專線的建設情況時,才來這裡待瞭5分鐘,
更何況,這個問題即便市長在這裡也很難當場拍板解決——他不能將教體局的規定變成一張廢紙,也沒辦法一夜之間在市區建起足夠多的學校,配備足夠的師資。
“真沒有一點辦法?我認識的人裡也有孩子是鄉下戶口、在城裡上學的,那是怎麼回事?”
作為一名接線員,我不能在錄音電話裡告訴他,人傢那是憑關系入的學。我隻能委婉地說:“不如去私立學校試一試,他們認錢不認戶口。”
也許是我無法說出口的事情他都懂,也註冊商標台中|註冊商標流程台中許他隻是想找一個傾訴的地方,在長達半個小時的通話中,他漸漸平靜下來:“好吧,我再去想想辦法,謝謝你。”
掛斷電話後,程燕過來告訴我,以後再接到類似的電話,不要說太多,把相關規定解釋清楚就可以瞭:“符合規定的交辦件,不符合的一律不予受理。我們這是代表政府形象的行政平臺,不是電臺的熱線電話。”
態度一定要好
9月關於孩子入學的問題紮堆,我們隻能拿著教體局的文件,一遍一遍地向傢長解釋,可仍然無法安撫他們的憤怒。
一個女人在電話裡大聲叫嚷:“你們光會念規定,有什麼用!我們不想聽規定,就想讓小孩上學!你把市長叫出來,我要跟市長說話!”
我環顧一周,到哪裡去給她揪一個市長出來?我隻好繼續跟她說那些車軲轆話,她越聽越急,便把一腔怒火發泄到我身上,而作為政府的代表,我卻不能還口。
接瞭幾天的電話,我開始想,這份工作的意義,難道就隻是反復解釋和承受斥責嗎?
在例行的周匯報上,戶口不合規的學生的上學問題引起瞭市政府重視。最終上級部門和教體局協調決定,擠出一部分名額,讓情況屬實、且必須在市區上學的孩子通過搖號,插班入學。
搖號那天,市八中的操場上人頭攢動,教體局的一個副局長親臨現場指揮,拿著小喇叭站在高處喊得聲嘶力竭,場面幾近失控。
搖號結束後,一位大嫂抽到瞭名額,可她還是不滿意,在電話裡繼續訴苦:“九中的校區那麼遠,我又不會騎車,接送不瞭孩子。我孩子上不成學,政府管不管?”
我有些無語:“原本農村戶口的孩子應該在戶口所在地上學,現在政府已經想辦法在市區給孩子分配學校瞭,你現在……”
“不管,不管,我不管!我不滿意,我要重新抽簽!”
我終於沒有壓住情緒:“重新抽簽?你先去問問今天八中操場上的上千傢長答應不答應!你孩子有學上已經很幸運瞭。市裡學校隻有這麼多,老師也隻有這麼多,市長又不能一下子變出個學校放在你傢門口!你隻管吵,但我告訴你,你的無理要求是不可能被滿足的。”
最後,那個大嫂又說瞭幾句狠話,悻悻地掛斷瞭電話。
我長舒一口氣,旁邊的方梅沖我豎瞭一下拇指。她是借調來的教師,在這裡工作一年多,早已磨平瞭棱角。隻有磨平棱角,才能做到“群眾激動的時候我不激動,群眾生氣的時候我不生氣”,不管事情能辦不能辦,態度一定要好。
暗藏玄機的井蓋
雖然辦公室的前輩不時會給我一些指點,但很多事情仍需要自己揣摩。
譬如一邊接聽電話,一邊就要判斷出是否形成“交辦件”。如果形成,就要開始在電腦上登記來電人的基本信息、主要訴求,更重要的,是要判斷出交辦件的具體承辦部門。雖然聽上去很簡單,可越簡單的事情往往內藏玄機。
有市民打電話來,說看到路上的井蓋丟失瞭。我一邊問具體路段,一邊在電腦上記錄,接著點擊“完成”,電腦自動將交辦件轉發到瞭對面的轉辦區。
沒一會兒,轉辦區就打來電話:“這井蓋是誰傢的?”
“嗯?”我被問懵瞭。
王主任意味深長地解釋:“你以為井蓋很簡單嗎?它可能是自來水廠的、電業局的、供暖公司的,也有可能是移動的、聯通的……我們一個交辦件發過去,人傢三四天回復過來,一句‘不是我們的’,我們就得再找下傢。如此幾次,井蓋可能十幾天都安不上去。”
“不過是一個井蓋,還一定要分清楚是誰傢的嗎?”
“當然,這是公傢的事。要是電業局替自來水廠安瞭一個井蓋,經手人回去怎麼報賬?自己貼錢嗎?”接著,王主任鄭重地總結,“群眾不管那麼多,他們隻知道打瞭電話,看井蓋卻遲遲安不上去,肯定要罵我們屍位素餐。下次,記得盡量問清楚現場群眾,提高辦理效率。”
我點點頭,虛心受教。
其實不光是井蓋,路燈也是一樣。譬如背街小巷的路燈屬於街道辦事處,大街上的路燈屬於住建局,小區的路燈歸屬物業管理。所以當市民投訴時,我既要問清楚路燈的具體位置,還要迅速判斷出負責的部門。
你們隻知道念文件嗎?
進入11月份後,北方進入供暖季,跟供暖相關的投訴件也多瞭起來。
有些老小區因為暖氣管道老化,熱力公司隻能緩緩加壓,以免管道崩裂,供暖效果自然不太好。可是熱力公司在和小區業主協調管道改造時,不少業主又不願意花錢,便打電話投訴熱力公司。
熱力公司在接到我們的轉辦件之後,倒也盡職盡責,主動上門為用戶測量溫度。凡是達不到16度的(供暖標準:18±2度),熱力公司承諾加壓,盡快提高溫度。
得到回復後,有些市民偃旗息鼓,有些則不依不饒。
一位大爺在電話中抱怨:“我聽說有些小區室內快30度瞭,大冬天還開著窗戶、穿著短褂。你說我傢隻有16、7度,就達到供暖標準瞭,這也太不公平瞭!”
我心想,大爺,能不能先把您傢裡的老式暖氣片改成地暖,再把四面漏風的獨院封閉嚴實?我把這話憋在肚子裡,說出來的是另一番話:“您看,市裡的文件是這樣寫的,凡是供暖溫度達到……”
“廢物!你們幹什麼吃的,隻知道念文件嗎?你工號是多少,報上來,我現在就要投訴你!”
“我們沒有工號。另外我是根據文件進行答復,沒有違規的地方。”
“你看看你什麼態度?不就是個接電話的,你把工號報上來,我不信今天還治不瞭你瞭……”
當時我缺少經驗,一怒之下就把電話掛斷瞭,讓這大爺的謾罵戛然而止。
很快,他的電話又打瞭進來,我繼續掛斷。然後這大爺跟我較上勁瞭,電話不停地打。
程燕發現情況不對,將電話接起來:“……對,我們的電話線路比較繁忙,不存在故意不接電話的情況……要找剛才的接話員?我也不知道剛才是誰接瞭你的電話,幾部電話是隨機轉接的,有什麼情況你可以向我反映……好的,你反映的情況我們一定會及時處理……”
程燕掛斷電話,又給我上瞭一課:有些要求明知道無法滿足,但還是不要直接對當事人說清道明,把話說委婉一些,時間久瞭,他那股勁頭也就散瞭。
市長不管,我就殺人
打個電話需要多少成本?兩毛錢。所以,不要希望市長熱線能夠解決真正的大事情。
王主任曾多次告誡我們,涉法案件不在受理范圍內:“行政單位沒有幹預公檢法辦案的權力。”
可這類求助電話卻不在少數,最常見的是交通事故。
按照交通事故的處理流程,交警部門在進行責任鑒定之後,會對雙方進行調解,如果不能和解,就等待法院的判決。這套流程走下來,少則兩三個月,多則一兩年,躺在醫院的傷者花錢如流水,這種情況下,等不及的傷者傢屬隻能向“市長”求助。
而接到這樣的電話,我們能做的,也隻是向交警隊發一個督辦函,交警隊的回復總是“正在盡力協調肇事方墊付醫藥費”——他們的權限也隻限於此,沒有權力強迫肇事方。
電話裡,常有傷者傢屬要求“市長”把“喪天良”的肇事者抓起來,讓“市長”去給他們要錢。言辭憤憤,或泣不成聲。接到這樣的電話,我隻能建議對方向紅十字會、慈善總會求助,先想辦法籌錢看病,再寬慰一番,僅此而已。
記得有次,接通電話後,我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:“我要殺人。”
那是一個小夥子的聲音。他傢位於我們這裡最偏僻的鄉鎮,那裡現在按正常途徑已經娶不上媳婦瞭,所以適齡男子都是從貴州、雲南“娶”。一個外地媳婦嫁過來後,再接二連三地把傢鄉的姐妹、親戚介紹過來,當然,彩禮也是高得令人瞠目。
電話裡的小夥子為瞭娶媳婦,花瞭20多萬。彩禮給瞭娘傢人,媳婦過來住瞭半年,人就跑瞭。他說之前村裡已經跑瞭好幾個“高價媳婦”,其餘沒跑的,都被傢裡人嚴防死守地看著。
“沒報警嗎?”我知道這事不歸我們管,但還是多問瞭一句。
“報瞭。警察抓瞭介紹人,開始說是詐騙案,可是現在又說證據不足,把人給放瞭。我去找介紹人要錢,他耍賴不給。20多萬啊,就這樣白白沒瞭!我現在錢沒瞭,媳婦也沒瞭,你們政府要是不管的話,我就把介紹人殺瞭,我也不活瞭……”
我不知道怎樣幫助他,隻能勸他珍惜生命,千萬不要沖動之下做出違法的事情。政府管得再寬,也沒辦法給他一個媳婦。
明坑易躲,也有事難辨
有時候,行政專線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,當作談判的砝碼。
我曾接到一個男人的投訴:移動公司施工,在他傢附近挖瞭一個坑,影響到瞭他的正常出行,要求移動公司將這個坑填上——聽起來很合理,所以我們及時給移動公司發瞭交辦件。
可過瞭幾天,這人又打來電話,說移動公司沒有來填坑,讓我們再催一下。
我們打電話詢問移動公司的分管領導,領導說他們早就派人去填坑瞭,但被投訴人阻攔,不許他們填坑,所以無功而返。原來,投訴人想自己填坑,並要求移動公司給他1000元的“填坑費”。移動公司拒絕瞭他,他便通過行政專線繼續給移動公司施壓。
投訴人第三次打電話催促時,我們將移動公司反映的情況和他對質,他支支吾吾起來。接話員告訴他,移動公司承諾會再次去填坑,如果還阻攔的話,行政專線將不會再受理他的投訴。最終,坑還是移動公司自己填上瞭。
有時候覺得隔著電話線也挺好的,當與求助人面對面時,他們裸露的情感會讓本該中立的我們產生偏頗。
有天,一個老大爺推開瞭辦公室的門,他衣著破舊,臉上滿是皺紋,頭發稀疏花白,不知道是怎麼打聽到這裡的。大爺一進門就要下跪,嚇得我們趕緊上前攙扶。
大爺拿起一張照片,上面是一個赤裸的孩子,後背和腿血淋淋的,慘不忍睹。大爺說,這是他的孫子,玩火燒傷瞭,現在在醫院裡搶救。爹媽不負責任,一個跑瞭,一個隻顧自己,他自己負擔不起醫藥費,想讓我們幫幫他。
我們聯系瞭市慈善總會,讓他拿著材料到那裡看看,老人感激地點點頭,步履蹣跚地走瞭。
他走後,我眼前一直晃動著孩子血紅的身體和老人滄桑的面孔,心裡像堵瞭一塊石頭。我從錢包裡拿出200元,追到大廳叫住他,把錢塞到他手裡:“拿著吧,不是什麼大錢……”
回去後,這件事情被王主任知道瞭,他批評瞭我:“首先,老人所說的事情都沒有經過核實,隻有一張照片,很可能是一個騙子;其次,要是開瞭這個頭,以後有困難的人都到這裡來要錢怎麼辦,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就打亂瞭?”
“年輕人啊,不要同情心泛濫。我們有我們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內容,不要超出本分。”
幼兒園裡突然消失的爸爸
能解決群眾的需求和困難,確實讓人愉快,隻是這樣的事並不多。
之前,一個4S店的經理打來電話,說店裡存的水沒用瞭,白白排出去可惜,希望我們能聯系市區環衛處,將這些水送給他們,我從中搭橋,環衛處出動車輛將水抽走,用於澆花澆樹。
還有一次,市裡愛心幼兒園的園長打來電話,說他們那裡有一個小朋友已經半年多沒人接瞭,幼兒園聯系不上傢長,也不敢把孩子丟下不管,無奈之下想到瞭我們。
電話是我接的,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理,就把情況匯報給瞭王主任,他很重視,要園長下午來辦公室將這個事情詳細談一談。
下午上班後,園長過來瞭。兩年前,一個單身爸爸把孩子送到幼兒園“周托”,但半年前,這個爸爸忽然莫名消失,再也沒來接過孩子。直到現在,孩子吃住都在幼兒園裡,衣服也是幼兒園老師捐贈的。
園長說:“孩子吃不瞭多少,幼兒園也負擔得起,關鍵是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啊,孩子生病瞭怎麼辦,他總要找到傢人啊!”
王主任和李主任陪同園長一起,去孩子傢裡、社區、派出所奔波瞭一下午,終於搞清楚事情原委:原來,孩子的父母當初並沒有登記結婚,生瞭孩子後,當媽的拍拍屁股走瞭,當爸的遊手好閑,半年前因為盜竊罪進瞭監獄,孩子就丟在瞭幼兒園。
經過協調,王主任在監獄裡見到瞭孩子的爸爸,希望能通過他找到孩子的媽媽,暫時把孩子管起來。可令人失望的是,孩子媽媽是外地人,和他早就失去瞭聯系。
好在後來我們輾轉找到瞭孩子的大伯,說服他在孩子爸爸坐牢期間暫時看管一下,才算是把這個孩子安頓下來。
事情暫時解決瞭,園長露出瞭笑容,我也難得感受到瞭這份工作的價值。
後記
一年後,我的工作有瞭著落,離開瞭行政專線。
這一年裡,由於經常接觸到負能量,又經常承受無端的指責,所以在鈴聲響起的一剎那,我竟然開始有些害怕,但心裡又不禁揣測,電話另一頭光怪陸離的世間百態裡,又有什麼麻煩事?
什麼都能治,卻又什麼都治不好,這就是“市長熱線”。
本文系網易獨傢約稿,享有獨傢版權授權,任何第三方不得轉載,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。
關於“人間”(the Livings)非虛構寫作平臺的寫作計劃、題目設想、合作意向、費用協商等等,請致信:thelivings@vip.163.com
題圖:VCG
">
市長熱線那頭,沒有市長
南風歌
8FBCA0F78537C490
1
見陳廣智之前我很緊張,在寢室裡拿著夾板一遍又一遍地燙著劉海兒,塗瞭手指甲,還用拙劣的技術化瞭妝。衣服換瞭好幾套,站在鏡子前反復照,不知道怎樣才能讓我看上去更漂亮。
在這之前,我和陳廣智剛在QQ上結束瞭50個小時沒日沒夜的聊天。而3天前,我們還是在大學校園裡碰面都不認識的陌生校友。
陳廣智在女生寢室樓下等我,我們沒看過彼此的照片,但當我跨出寢室大門,看到他的第一眼時,內心就有個聲音告訴我:就是他瞭。幾分鐘後,我和他當場決定:在一起。
我們倆這個默契的共識達成於2009年的5月一個黢黑的夜晚,可好多年後想起來,還覺得是個艷陽天。後來,陳廣智從他的視角,還原瞭第一次見到我時的場景——
“就記得那晚約你去燒烤攤吃宵夜,你一串接一串地吃,頭都沒抬一下,還一個勁兒地說‘好吃,好吃’,我心想,你是不是沒吃晚飯哦,有那麼餓嗎?”
我抑住怒火,微笑著幫他回憶我當時精致的妝容,他認真思考一番,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,但隨即補瞭一句:“想起來瞭!吃燒烤的時候,你嘴唇上的口紅都花瞭。不過看你吃得那麼香,我當時都不忍心提醒你瞭。”
接著,他順口反問我,為何會輕易地接受一個認識不過3天的人,我抽絲剝繭,發現我對他動心的點,竟是見面前一天的深夜,我們聊天時他突然打瞭一句:“你稍等下,我有點餓瞭,出去買個燒烤。”
當時我的寢室早已鎖門熄燈,一個“燒烤”,把我饞得百爪撓心。我躺在寢室的二層床上,猛咽瞭幾下口水,腳蹬在天花板上,忽然有個念頭在我腦袋裡瘋狂冒泡:他要是我男朋友就好瞭,至少能半夜幫我打包一份燒烤。
陳廣智聽完我的回答後哭笑不得:“那你怎麼不去找後門賣燒烤的那個小哥?近水樓臺先得月,包你吃個夠。而且,每次看你和他聊天聊得也挺嗨,你咋不和他談戀愛呢?”
我想瞭下,認真地回答他:“那小哥太愛吃瞭,邊烤邊吃,我怕搶不過他。”
陳廣智敲瞭一下我的腦袋,表示從來沒見過這麼好吃的人,“還是個女生!”他又補瞭一句。
對於我的這張“好吃嘴”,那時候的陳廣智並不能和我產生共鳴。他來自江蘇徐州,那是座歷史底蘊深厚的城市,自古以來就是兵傢必爭之地,在那裡長大的他,並不能對成都的安逸感同身受。
2
陳廣智與成都的淵源,要追溯到2007年。
那年夏天,他趴在中國地圖上,手指在“哈爾濱”和“海南”之間來回遊走,挑選未來四年生活學習的大學。但與其說是選大學,不如說是選城市:首先要離傢遠,不能一腳油門就被傢長探望;其次,城市要宜居。
忽然,陳廣智的腦海裡蹦出瞭“少不入川”四個字,他認為這是對一個城市的褒獎,便順手把四川也納入選擇范圍。
那時,手機還不夠智能,不能支持陳廣智隨意放大電子地圖、把他用10分鐘就決定好要去的城市看個透。他也萬萬沒想到,自己隨意填寫的第三志願最終會將他錄取。不僅如此,在那座陌生的城市,還會遇到一個我,徹底改變瞭他以後的生活軌跡。
2007年8月開學報道前一天,坐瞭30多個小時的火車,陳廣智和他父親輾轉來到學校時,倆人已饑腸轆轆。
學校後門有條小吃街,白天僅有連排的商鋪營業。街邊的臺階上佈滿瞭成片的油漬,暗示著此地別樣豐富的夜生活。
落日餘暉中,路邊攤紛紛開張,學生們蜂擁出巢,整條街瞬間換瞭風格。小攤一傢挨著一傢,燈火通明,亮度逼人,霸占瞭整條街巷。有老板操著四川話,中氣十足的吆喝聲;有三五成群的學生,把牛皮吹上天的聲音;有食材在熱油上煎炸的“嗞嗞”聲;還有急躁的汽車喇叭聲,司機們盼著能在密密麻麻的路邊攤中擠出一條小道。
打小陳廣智便跟著做生意的父親一同混跡在各大飯局上,父子倆一致認為路邊攤是“臟、亂、差”的代名詞,兩個大老爺們兒窩在路邊吃小攤兒,實在不體面。於是兩人眉頭緊鎖,快速地通過小吃一條街,拐進一傢稍顯高檔的川菜館。
聽說川菜以“辣”出名,兩人商量著,怕初到成都腸胃不適應,便順著菜單想找些清淡的。兩人同時鎖定瞭“水煮肉片”這道菜名——“水煮的,一定清淡又養生。”
當老板端上來那盆蓋著厚厚一層花椒和辣椒、在滾燙的油中爆發出“呲啦呲啦”聲音的肉片時,從江蘇來的父子倆不由一愣,果不其然,嘗瞭一口便被嗆出眼淚。
陳廣智猛灌瞭幾口白開水,心裡更是一通抱怨:自己選的城市一點都不“宜居”,連一個“白水煮菜”都那麼辣。隻是礙於面子,陳廣智不願向父親承認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。
隻是後來,陳廣智告訴我,吃完那頓飯,他就當場決定:畢業後一定不能留在成都,“這個城市實在是太不對胃口瞭”。
3
我和陳廣智確立戀愛關系後的第一頓飯,就上演瞭一場關於吃的“博弈”。
星期六的早晨,他如約到寢室樓下接我。這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,雖然在QQ上24小時不間斷地廢話連篇,可面對面還是不免有些尷尬。
陳廣智是個1米86的大高個兒,他在我的前面三步並作兩步地走,我跟在後面都快要跑斷氣瞭,也沒好意思開口讓他等等我。直到他無意間回過頭,見我在喘著粗氣,就用蹩腳的四川話問:“你咋子瞭?那麼累呢?要不要坐下來吃口東西緩緩?”
我這才意識到,自己對他的聲音非常陌生,不標準的四川話從他嘴裡冒出來,聽上去很滑稽。“沒關系,你可以和我說普通話。”剛說完就發現自己把話題帶偏瞭,趕緊補瞭一句:“好,那坐下來吃點東西吧。”
陳廣智提出去學校附近的一傢西餐廳,那是學生界的“高規格”餐廳,招待“貴賓”的首選,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對我的重視。我聽瞭後卻像個泄瞭氣的皮球,但由於兩人還不熟,我並沒有提出異議。我點瞭一份最便宜的牛排,放在口中如同嚼蠟,吃瞭一塊便放下刀具。
那天傍晚,陳廣智讓我決定晚上吃什麼。我抬起頭,遞上一個善解人意的微笑:“不用不用,我吃什麼都可以。”腳步子卻一個勁兒地往學校後門的小吃街挪,一邊走,一邊用餘光快速地掃過周圍的路邊攤,腦袋裡瘋狂盤算著要臨幸哪一傢才能安撫我的胃。
最後,我選瞭一傢窩在墻角邊上的路邊攤吃冒菜。落座時,我明顯看到陳廣智環顧瞭下四周,露出瞭猶豫的神情。可是,此時冒菜的香辣味已然傳到瞭我的鼻腔裡,饞得我顧不瞭那麼多瞭,便假裝沒看到。
冒菜是四川特色小吃,把土豆片、藕片、紅苕粉、鴨血、豆芽等素菜,裝在用竹子編成的簍裡,老板借助腕力,將竹簍放入用火鍋底料和高湯熬制而成的湯底裡“冒”。當菜品滲入湯汁後打撈出鍋,放入碗中,再配上小米辣、辣椒油、花椒等佐料,舀上一勺湯底,把香辣提升到極致。
陳廣智問我為什麼喜歡吃冒菜:“這樣的小攤兒很不衛生。”
“其實我愛吃火鍋,可是一個人去吃火鍋太尷尬瞭,最多吃一兩個菜就飽瞭,冒菜多好,十多種菜全有,隨時都可以感受私人火鍋般的頂級待遇。”我說完,陳廣智笑著看著我,沒有接話,我又補瞭一句,“你聽過這麼一句話麼,‘冒菜是一個人的火鍋,火鍋是一群人的冒菜。’所以啊,其實火鍋冒菜都一樣,就看是自己吃,還是和別人一起吃。”
“你要是愛吃火鍋,我以後就經常陪你去吃。當然啦,我吃白味湯底。我聽說你們四川人覺得吃白味是對火鍋的侮辱,你可別嫌棄我哈。至少我陪你,以後都就不用吃‘一個人的火鍋’瞭。”陳廣智撓著頭,露出害羞的表情。
對我來說,這是陳廣智對我說的第一句情話。
我夾起一片藕送進嘴裡,在牙齒的咬合下,滲出一絲絲的甜味,配著香辣傳到胃裡,胸膛暖呼呼的。原來和喜歡的人一起吃飯,竟然可以這麼開心。
“2009年5月19日,我和陳廣智一起吃的冒菜,比生命中任何一次都好吃。”我在那天的日記裡這麼寫道。
4
陳廣智在和我一起吃瞭約400頓飯之後,成功被洗腦,儼然成為我攻克美食道路上的幫兇。
剛在一起的那一年,團購網站還是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新興產業。那時候每天最開心的事,就是一口氣把收藏的20多傢美食團購網全部開啟,寢室網絡不佳,我會歸正瞭鼠標和鍵盤,坐直身板兒等待網頁緩沖出來。然後挨傢篩選,看圖片和口碑。但凡有評論表示這傢食物好吃,我一定會拉著陳廣智去嘗一嘗。
父親從小對陳廣智的教育就是:凡事不要拖拉,時間要用在節點上。因此,陳廣智總是對我趕公交車,穿梭在成都各大街小巷尋找美食的行為嗤之以鼻。
而我從小路癡,在生活瞭20多年的城市也時常會迷路。憑借著這個借口,陳廣智隻能妥協。他負責找路,我負責吃,這成瞭我們異於常人的默契。
我挖地三尺才找到的美食,經常需要排隊。陳廣智對此非常不理解:“吃飯不就是填飽肚子的事兒嗎?在我傢那邊,沒人會把時間浪費在排隊吃飯這件事兒上。能吃就進,不能吃就走。這些人,真是閑的。”
“吃飯是一種享受,排隊是對美食的尊重,這是最有儀式感的事!”我據理力爭。
“那你咋不戴上紅領巾去吃飯?那樣更有儀式感。”我時常被陳廣智懟得啞口無言,但往往是他一邊嫌棄我,一邊陪我嘗試那些“有儀式感的”的美食。
那段時間我幾乎嘗遍瞭成都所有的“網紅火鍋”。我跟陳廣智說我小時候經常問父母為啥不開火鍋店,陳廣智給瞭我一個答案:“要是開瞭火鍋店,還不被你天天吃給吃垮瞭。”
有次,他陪我排隊時,拉著同在排隊的人,在火鍋店門口玩起瞭鬥地主。我嘲笑他:“你終究還是成瞭你曾經最討厭的那類人。”他狡黠一笑,回敬道:“別人是近朱者赤,和你一起,是近豬者豬。”
此話也不無道理,我從小就無辣不歡,火鍋一定不能配油碟,那樣會破壞火鍋底料的厚重感,原湯加幹辣椒面才是完美搭配。要是能再舀上一勺小米辣,鮮辣與麻辣雙重刺激,更是會調動起全身的細胞。陳廣智在我的帶領下,可以駕馭任意一種四川特色的辣。曾經把他傷害得很深的“水煮肉片”,後來對於他來說隻能算作辣味鏈上的最底端。
5
成都真正的美食,大多數是路邊攤,隱藏在小巷中。
我時常逗陳廣智:“這些藏在卡卡角角(四川話,角落,音kakaguoguo)的路邊攤,你看美食攻略是完全找不到的,隻有我這種本地人才能搜刮得出來。我忽然發現你真是居心叵測,你找我,就是為瞭讓我帶你去吃這些正宗的路邊攤兒吧?”
陳廣智不屑一顧:“你以為我和你一樣,就那點出息啊?別人找對象是看車看房看戶口,到你這兒,就為一口吃的瞭。”
張奶奶的攤兒就是我們的老窩之一。這裡最開始賣的是狼牙土豆,業務壯大之後,又加瞭涼面、冰粉、燒烤、冒菜等。
我和陳廣智時常熟練地搬來小桌,放在墻角,窩坐在跟前。周圍是鬧哄哄的中學生,匆匆買瞭就走,他們有時會多看我們幾眼,陳廣智窩在一群穿著統一校服的半大孩子堆裡,的確很突兀。
前幾年,張奶奶在擺攤的時候出過一場車禍。一個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司機將車輪碾上瞭路邊的臺階,撞翻瞭攤位。正在削土豆皮的張奶奶來不及躲避,頭部受傷,以至於現在的記憶力很差。
雖然我們多次光顧過張奶奶的路邊攤,但她每次見我還是會致歉,表示忘記瞭我的口味。陳廣智則習慣性地在一旁提醒:“張奶奶,幫我女朋友多放點小米辣,不要客氣,直接給她拌成‘超級變態辣’,土豆剛過心就撈,一定要脆。不要味精,謝謝。”
每次陳廣智挺不好意思地說完這一長串的口味備註,張奶奶就笑盈盈地表示,下次一定記得。盡管如此,幾年的時間裡,這情景總是循環上演。
張奶奶拌的狼牙土豆(作者供圖)
2011年,陳廣智大四的那個寒假,我跟他回瞭次徐州。那裡有成都少見的大雪,蓋住馬路。牙膏凍得需要用熱水燙一下,才能擠出來。戴隱形眼鏡也成為我每日的一項挑戰。
陳廣智的傢鄉飲食口味清淡,幾乎沒有辛辣。他們愛吃羊肉,幾乎每頓都不落。而在成都,隻有“冬至”那一天會喝羊肉湯,我因為吃不慣羊肉的膻味,每次都會避開。我用真空袋打包的鹵兔頭,也沒人願意和我分享——大傢認為吃兔子是件很殘忍的事。
陳廣智怕我吃不慣,就提出帶我去掃蕩我最愛的路邊攤。
陳廣智高中門口也有一條小吃街,他熟絡地和老板們打著招呼,並熱情地向大傢介紹“這是我的女朋友”。老板們聽說我是個“川妹子”,主動提出要在“蛙魚”裡加辣椒。
“蛙魚”是徐州的一種形同小魚的面食,口感爽滑,自帶酸甜口味。我嘗瞭一口,並沒有吃出期待的辣味。我在心裡拼命對自己暗示:這是陳廣智喜歡的傢鄉菜,我要喜歡,以後要適應的還有很多。
晚上,我一個人溜到小區門口,光顧瞭一傢我白天瞥見的名為“四川麻辣燙”的店鋪。老板娘是成都人,嫁給瞭一個徐州人,從此在這生活。她曾在成都開過一傢冒菜館,我吃第一口時,就嘗到瞭自己熟悉的味道,頓時胃口大開。
隻是吃著吃著,我忽然對自己很失望,停下瞭筷子。或許自己和“四川麻辣燙”一樣,於這座城市而言,都是多餘的。
我吃到一半,陳廣智找到瞭我。老板娘聽說我也是成都人,絮絮叨叨講瞭很多:她來徐州後,什麼都吃不慣,才想著把自己在成都的事業帶到這邊來,做個念想:“有這個鋪子,我才沒那麼想傢。”
那頓飯,我們都沒有說話。
陳廣智的父親希望兒子能回傢發展,子承父業,在這個理由背後,還藏著那句中年男人難以開口的:兒子,爸想你瞭。陳廣智也褪去瞭四年前的那份浮躁,那顆四海為傢的心,早已被認定為是一種不負責任。
他不願把背井離鄉的包袱丟給我,經過幾個月的掙紮,在畢業之際,決定自己獨自回傢。
回傢就回傢吧,沒事,就這樣吧,能有什麼事。我想。
6
雖然自認為沒什麼,但身體還是誠實地出現瞭狀況。
自陳廣智回傢的那一刻,我仿佛失去瞭味覺,吃什麼都覺得毫無滋味。在他回傢後的第21天,我的兩個閨蜜搞瞭場“尋味之旅”,想拖我離開這場失戀的暴風雨。
兩個姑娘拉著我來到張奶奶的路邊攤,張奶奶察覺到我的反常,把狼牙土豆端給我時,順勢坐在瞭我旁邊的小凳子上,用身上的圍兜擦瞭擦手:“丫頭,你那個絕世好男朋友咋沒來?”
我有些詫異,張奶奶竟然用瞭“絕世好男朋友”這樣新潮的詞,而更讓我詫異的是,記不得我口味的她,竟然記得陳廣智。
“我們分手啦,張奶奶,他回他自己的城市啦。”我故作輕松地回答。
“咋個分開瞭?他對你那麼好。為啥子喃?”張奶奶是個急性子,和我傢院壩裡的老奶奶們一樣,熱情、單純、又八卦。她從圍兜裡抓出一大把零錢,遞給她女兒,準備專心聽我講述。
被一個不算熟悉的長輩問到感情問題,我有些不知道該如何接話。
張奶奶握住我的手說道:
“他真是個絕世好男朋友,每次來給你打包狼牙土豆時,我小女兒都會這樣念叨一遍。
“張奶奶我老瞭,手腳也不麻利,我都讓小女兒幫我提前炸好三大鍋的土豆,再拌好三種口味。這樣來一人,舀一碗,夠賣大半天勒。每次你男朋友來,都喊我單獨給你炸一小碗,說那樣才是脆土豆,才能拌出你喜歡的口味。
“有時候趕上學生放學的點兒,我們啊,根本莫得空單獨弄,他有時還親自切蔥,個人搗蒜,等我們忙過這陣,再喊我單獨給你拌。有時候,我看他那麼大高個子,站在墻角切土豆,我都不忍心。他還傻笑,說女朋友好養活,吃個土豆就笑瞇瞭。
“我傢開瞭有10年瞭,啥子顧客都見得多咯。很多小年輕談朋友,女娃娃喜歡吃我們這種攤攤兒,男娃娃卻看不上。有的還躲多遠,覺得掉價。也是,哪個小男娃娃不在乎點兒面子喃?”
我無法接話。
我低著頭,用竹簽插瞭好幾坨狼牙土豆,一口氣吞下。土豆炸軟瞭,在嘴裡混成一大團糊糊,吞不下去,吐不出來,卡在喉嚨裡,眼淚噎瞭出來。
7
兩年的接觸,我怎麼會不知道陳廣智是個多麼溫暖的人呢。
大三的時候,陳廣智吃瞭一個月的方便面,存錢給我買瞭一條裙子,699元,是我一個月的生活費。我舍不得,大發雷霆,讓他立馬去退。他沒料到我如此反應,隻得依著我。
陳廣智站在銷售阿姨面前,表示要退貨。店員瞬間提高音量,來回擺手,表示“衣服出售概不退貨”,僵持不下,最後把陳廣智晾在瞭那裡。他提著袋子,站在女裝店鋪裡,低著頭,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。最終,店員嫌棄他妨礙生意,同意退貨。
陳廣智捏著那699元,遠遠地向我招手,笑著跑到跟前。我的歉意還未表達,他先向我道歉:自己不該拿著父母給的生活費送我禮物,他要做的是畢業後努力工作,靠自己的雙手,讓我過上更好的生活。
“他不是說畢業後要努力工作,讓我過得更好嗎?他現在又跑到哪裡去瞭……”
張奶奶沒有回答我。或許她答瞭,我沒有聽見。我的眼淚刷刷地流,四周死一般寂靜。
陳廣智回傢後,並沒有忙著找工作,而是天天窩在傢裡打遊戲、睡覺、和老同學去籃球場打球。打完籃球,老同學們常常會約著在一起去吃宵夜,“戒瞭。”他一次都沒有去過。
他不僅戒瞭宵夜,連一日三餐也是能省則省。
一個月的時間,陳廣智瘦瞭15斤。所以當他頂著一臉胡渣子,再次跨入“四川麻辣燙”時,老板娘竟沒有認出他。
他打包瞭一份麻辣燙,還讓老板娘用小口袋額外裝瞭好幾勺辣椒面,“怎麼吃都不好吃,越看那個辣椒面,就越像紅磚末兒,倒胃口”。
那段時間,陳廣智學會瞭喝酒。仿佛自己的失眠可以借助酒精得以緩解。但喝瞭酒,還是睡不著。一次,陳廣智半夜起床,切瞭一塊固體火鍋底料,丟在鍋裡,和方便面一起煮。火鍋底料是前幾天在網上買的,是成都一傢隨處可見的火鍋連鎖店生產的袋裝底料。
拌著濃厚的辣味,他連吃瞭幾口。不知道是吃得太急,還是餓太久瞭,胃裡一陣翻滾,沖進廁所吐瞭起來。
陳廣智按下馬桶上的按鈕,“嘩——”,他忽然覺得一身輕松,好像有一盆水,“嘩”地一聲把他從頭淋到腳。
他突然想明白瞭,做瞭一個決定。
8
2011年8月底,陳廣智又回到瞭我的城市,像是過瞭一個普通的暑假,回成都來報道瞭。
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:“我回傢後竟然吃不慣傢鄉菜瞭,兩個月沒吃辣椒,憋得臉上冒起瞭痘痘。我每天都在想成都的美食。”沒等我開口,又說瞭句,“更想你。”
“回傢後,我什麼都吃不下去。每天都在擔心,擔心你想吃東西瞭,沒有人給你買,怕你餓著,怕沒有人照顧你……現在看你也沒餓瘦,我還挺失望的,我是不是想多瞭?”陳廣智認真地問我。
我“噗呲”一下笑出聲,笑著笑著,又撅著嘴開始流眼淚。我沒有回商標登記查詢台中|商標登記費用台中答他,隻想讓他好好抱抱我。我個子不高,臉正好貼在他的胸膛上,聽著心臟在我耳邊怦怦跳動。
從那時起,我恢復瞭味覺。
陳廣智兌現瞭他的承諾,在成都找瞭一份工作,工作之餘我們繼續嘗試各路美食,成都遍地都有我們的腳印。畢業多年後,我們仍時常回到大學,隻為回味那些年被我們寵幸的路邊攤。
泡椒魚米線的老板,還是會特意為我挑一個魚泡;有傢冒菜館,明明有著自己的招牌,由於門口掛著一副對聯——“山不在高有仙則名,店不在小有辣則靈”,被我們倆“山不在高”地叫瞭好幾年;還有最愛的一傢火鍋店,春去秋來,我們習慣性地坐在靠窗的位置,翹首等待原湯在鐵鍋裡冒出的一個泡兒。第一筷子永遠是夾千層肚,倒計時15秒起鍋,陳廣智燙得那份會第一時間夾到我的碗裡。
後來,我們還把路邊攤文化延伸到瞭其他地方,我們一同去瞭泰國,窩在大排檔前,老板比劃著為我們推薦瞭一個泰式湯鍋。當高聳的銅鍋端上桌,正好擋住瞭我面前的陳廣智,我和陳廣智同時搬著小凳子挪向瞭同一個方位,肩並著肩,擠在一起開吃。
對面街上人來人往,被太陽烤得發燙的地面,騰起熱浪,撲進眼睛裡,暖暖的。
9
後來,我和陳廣智再也無法盡情流連於路邊攤瞭——我們的小小陳出生瞭。
小朋友是個十足的搗蛋大王,初為父母的我們,手忙腳亂,很難安份地吃完一頓飯。每次寶寶在飯桌前抗議,陳廣智就會假裝嚴肅地說:“你別鬧媽媽,有種沖我來啊,小子!”
寶寶咿呀學語,最先清晰蹦出的兩個字,除瞭“台中註冊商標推薦|台中註冊商標事務所推薦媽媽”、“爸爸”,還有一句“好吃”——他算是徹底繼承瞭我的好吃嘴。
如今,陳廣智時常需要出差,我舉著手機和他視頻,叫兒子過來看爸爸。小傢夥傲嬌得很,任陳廣智怎麼喊他,他都自顧自地玩著手邊的玩具。隻有一個辦法能瞬間抓住他的註意力,我說:“小子,快來看爸爸正在吃什麼呢。”
陳廣智會配合著咂嘴:“嗯,好吃!真好吃!”
寶寶立馬奔瞭過來,伸個腦袋在手機面前,“爸爸,你在吃啥好吃的呀。你快回來吧,我想你瞭,我好乖,爸爸給我買好吃的回來吧。”
等小小陳長大些後,陳廣智會領著兒子,和我一起光顧張奶奶傢的路邊攤。張奶奶的曾孫子很喜歡和小小陳一同玩耍,有時候,張奶奶還會送一碗新鮮出爐的白味狼牙土豆給兒子解饞。
上個月,在吃狼牙土豆的時候,兒子摟著我的脖子,問陳廣智:“爸爸,我和老媽都是好吃嘴,你愛我們嗎?”
“當然,我好愛你們。”
本文系網易獨傢約稿,享有獨傢版權授權,任何第三方不得轉載,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。
“人間有味”長期征稿,歡迎大傢將自己與食物有關的文字、圖片稿件投遞至人間郵箱:thelivings@163.vip.com 我們在這裡等你。
題圖:golo
插圖:作者供圖
2013年,我市和上級地級市的“市長熱線”聯合辦公,增加瞭網絡投訴平臺,整合成為行政專線,業務擴大後,需要再招一批工作人員,我便從9月開始,到那裡工作瞭一年。
市政府的行政辦公區位於新修建的紫薇大道上,行政專線占用瞭一樓東頭的3個辦公室,最大的有一個教室大小,是“接辦區”,對面的兩間小辦公室分別是“轉辦區”和“回訪區”。接待我的是負責接辦區的王主任,30多歲,中等個子,面相和氣——後來我才知道,凡在這裡待的時間長一些,能負點責的,都會被冠以“主任”的稱呼。
行政專線由市政府和市紀委雙重領導,部門屬性不明,成員構成也頗為復雜。這裡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是李主任,他本身是市紀委督察室的主任,平時工作重心在紀委,很少來這裡,所以日常工作便由王主任和張主任負責。王主任正式編制在畜牧局,借調來此,是當初專線成立時的兩大元老之一;李主任則是從鄉鎮借調來的教師,負責轉辦和回訪,定期向市政府進行情況匯總。其餘十幾個工作人員,大部分都是從學校抽調來的老師,也有小部分像我這樣,屬於勞務派遣,由勞務公司統一發放工資。
所以說,這是一個沒有編制且不需要發工資的正式單位。
作為菜鳥,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接辦區接電話。王主任說,當初專線成立時,他的工作也是從接電話開始的。推開接辦區辦公室的門,裡面有4個30多歲的婦女。王主任簡單介紹瞭下,又吩咐一個叫程燕的大姐帶我幾天,說罷轉身出去瞭。我有些不好意思,拘謹地坐在王主任指定的位置上。
程燕看上去是個開朗的人,她告訴我:“桌上的電話是和電腦相連的,每個電話接進來,都會在電腦上顯示出來電的基本信息,當然,電腦上也會留下相關記錄。”她又特別提醒我:“每一次通話都會被錄音,所以說話時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措辭,不要給人留下把柄,更要避免遭到投訴。”
正在這時,鈴聲響瞭。她示意我將帶著話筒的耳機戴好,然後按下瞭接聽鍵。
就這樣,沒有崗前培訓,沒有工作經驗,我的接話員生涯開始瞭。
電話這頭沒有市長
電話對面是一個男人的聲音。他是一個賣菜的小販,當時正是開學季,適齡的孩子已經開始上課,而他的孩子還沒有學可上。
按照教體局的規定,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需要在戶口所在地報名上學。他和孩子的戶口還在鄉下老傢,不在市裡,所以隻能回鄉下上學。
我把教體局的規定向他解釋瞭,可顯然他打電話過來不是聽我解釋的:
“你看,我們兩口子每天凌晨4點多就得去市場批發,在街上轉悠一天才能賣完,全傢人都得靠這個吃飯。我們要是把孩子送回老傢,那就得有一個人回去看孩子,生意就做不成,我們還怎麼生活……”
“我聽說市裡的學校是允許借讀的,你幫我問問,到底怎麼個借讀法兒。隻要孩子能上成學,出錢我們也願意。唉,我們就是個賣菜的,城裡一個朋友也沒有,傢裡也沒有有本事的親戚。眼看著別的小孩都去上學瞭,孩子在傢裡鬧個不停,求求你們給我想想辦法吧!”
我仔細看著教體局的文件,一行行文字清晰冷靜——“隻有外地務工人員的子女可以憑借相關證明,在市區學校借讀”。
男人憤憤不平:“外地人都可以在城裡上學,我們本地的鄉下人卻不能,這是什麼狗屁規定!你們就不能讓市長管管嗎?”
“讓市長管管”這句話在以後的無數個電話中頻繁出現,很多打來電話的人都以為這頭就坐著市長,可以滿足他們各種各樣的需求。可事實上,在我工作的一年裡,市長隻有在陪同上級領導考察行政專線的建設情況時,才來這裡待瞭5分鐘,
更何況,這個問題即便市長在這裡也很難當場拍板解決——他不能將教體局的規定變成一張廢紙,也沒辦法一夜之間在市區建起足夠多的學校,配備足夠的師資。
“真沒有一點辦法?我認識的人裡也有孩子是鄉下戶口、在城裡上學的,那是怎麼回事?”
作為一名接線員,我不能在錄音電話裡告訴他,人傢那是憑關系入的學。我隻能委婉地說:“不如去私立學校試一試,他們認錢不認戶口。”
也許是我無法說出口的事情他都懂,也註冊商標台中|註冊商標流程台中許他隻是想找一個傾訴的地方,在長達半個小時的通話中,他漸漸平靜下來:“好吧,我再去想想辦法,謝謝你。”
掛斷電話後,程燕過來告訴我,以後再接到類似的電話,不要說太多,把相關規定解釋清楚就可以瞭:“符合規定的交辦件,不符合的一律不予受理。我們這是代表政府形象的行政平臺,不是電臺的熱線電話。”
態度一定要好
9月關於孩子入學的問題紮堆,我們隻能拿著教體局的文件,一遍一遍地向傢長解釋,可仍然無法安撫他們的憤怒。
一個女人在電話裡大聲叫嚷:“你們光會念規定,有什麼用!我們不想聽規定,就想讓小孩上學!你把市長叫出來,我要跟市長說話!”
我環顧一周,到哪裡去給她揪一個市長出來?我隻好繼續跟她說那些車軲轆話,她越聽越急,便把一腔怒火發泄到我身上,而作為政府的代表,我卻不能還口。
接瞭幾天的電話,我開始想,這份工作的意義,難道就隻是反復解釋和承受斥責嗎?
在例行的周匯報上,戶口不合規的學生的上學問題引起瞭市政府重視。最終上級部門和教體局協調決定,擠出一部分名額,讓情況屬實、且必須在市區上學的孩子通過搖號,插班入學。
搖號那天,市八中的操場上人頭攢動,教體局的一個副局長親臨現場指揮,拿著小喇叭站在高處喊得聲嘶力竭,場面幾近失控。
搖號結束後,一位大嫂抽到瞭名額,可她還是不滿意,在電話裡繼續訴苦:“九中的校區那麼遠,我又不會騎車,接送不瞭孩子。我孩子上不成學,政府管不管?”
我有些無語:“原本農村戶口的孩子應該在戶口所在地上學,現在政府已經想辦法在市區給孩子分配學校瞭,你現在……”
“不管,不管,我不管!我不滿意,我要重新抽簽!”
我終於沒有壓住情緒:“重新抽簽?你先去問問今天八中操場上的上千傢長答應不答應!你孩子有學上已經很幸運瞭。市裡學校隻有這麼多,老師也隻有這麼多,市長又不能一下子變出個學校放在你傢門口!你隻管吵,但我告訴你,你的無理要求是不可能被滿足的。”
最後,那個大嫂又說瞭幾句狠話,悻悻地掛斷瞭電話。
我長舒一口氣,旁邊的方梅沖我豎瞭一下拇指。她是借調來的教師,在這裡工作一年多,早已磨平瞭棱角。隻有磨平棱角,才能做到“群眾激動的時候我不激動,群眾生氣的時候我不生氣”,不管事情能辦不能辦,態度一定要好。
暗藏玄機的井蓋
雖然辦公室的前輩不時會給我一些指點,但很多事情仍需要自己揣摩。
譬如一邊接聽電話,一邊就要判斷出是否形成“交辦件”。如果形成,就要開始在電腦上登記來電人的基本信息、主要訴求,更重要的,是要判斷出交辦件的具體承辦部門。雖然聽上去很簡單,可越簡單的事情往往內藏玄機。
有市民打電話來,說看到路上的井蓋丟失瞭。我一邊問具體路段,一邊在電腦上記錄,接著點擊“完成”,電腦自動將交辦件轉發到瞭對面的轉辦區。
沒一會兒,轉辦區就打來電話:“這井蓋是誰傢的?”
“嗯?”我被問懵瞭。
王主任意味深長地解釋:“你以為井蓋很簡單嗎?它可能是自來水廠的、電業局的、供暖公司的,也有可能是移動的、聯通的……我們一個交辦件發過去,人傢三四天回復過來,一句‘不是我們的’,我們就得再找下傢。如此幾次,井蓋可能十幾天都安不上去。”
“不過是一個井蓋,還一定要分清楚是誰傢的嗎?”
“當然,這是公傢的事。要是電業局替自來水廠安瞭一個井蓋,經手人回去怎麼報賬?自己貼錢嗎?”接著,王主任鄭重地總結,“群眾不管那麼多,他們隻知道打瞭電話,看井蓋卻遲遲安不上去,肯定要罵我們屍位素餐。下次,記得盡量問清楚現場群眾,提高辦理效率。”
我點點頭,虛心受教。
其實不光是井蓋,路燈也是一樣。譬如背街小巷的路燈屬於街道辦事處,大街上的路燈屬於住建局,小區的路燈歸屬物業管理。所以當市民投訴時,我既要問清楚路燈的具體位置,還要迅速判斷出負責的部門。
你們隻知道念文件嗎?
進入11月份後,北方進入供暖季,跟供暖相關的投訴件也多瞭起來。
有些老小區因為暖氣管道老化,熱力公司隻能緩緩加壓,以免管道崩裂,供暖效果自然不太好。可是熱力公司在和小區業主協調管道改造時,不少業主又不願意花錢,便打電話投訴熱力公司。
熱力公司在接到我們的轉辦件之後,倒也盡職盡責,主動上門為用戶測量溫度。凡是達不到16度的(供暖標準:18±2度),熱力公司承諾加壓,盡快提高溫度。
得到回復後,有些市民偃旗息鼓,有些則不依不饒。
一位大爺在電話中抱怨:“我聽說有些小區室內快30度瞭,大冬天還開著窗戶、穿著短褂。你說我傢隻有16、7度,就達到供暖標準瞭,這也太不公平瞭!”
我心想,大爺,能不能先把您傢裡的老式暖氣片改成地暖,再把四面漏風的獨院封閉嚴實?我把這話憋在肚子裡,說出來的是另一番話:“您看,市裡的文件是這樣寫的,凡是供暖溫度達到……”
“廢物!你們幹什麼吃的,隻知道念文件嗎?你工號是多少,報上來,我現在就要投訴你!”
“我們沒有工號。另外我是根據文件進行答復,沒有違規的地方。”
“你看看你什麼態度?不就是個接電話的,你把工號報上來,我不信今天還治不瞭你瞭……”
當時我缺少經驗,一怒之下就把電話掛斷瞭,讓這大爺的謾罵戛然而止。
很快,他的電話又打瞭進來,我繼續掛斷。然後這大爺跟我較上勁瞭,電話不停地打。
程燕發現情況不對,將電話接起來:“……對,我們的電話線路比較繁忙,不存在故意不接電話的情況……要找剛才的接話員?我也不知道剛才是誰接瞭你的電話,幾部電話是隨機轉接的,有什麼情況你可以向我反映……好的,你反映的情況我們一定會及時處理……”
程燕掛斷電話,又給我上瞭一課:有些要求明知道無法滿足,但還是不要直接對當事人說清道明,把話說委婉一些,時間久瞭,他那股勁頭也就散瞭。
市長不管,我就殺人
打個電話需要多少成本?兩毛錢。所以,不要希望市長熱線能夠解決真正的大事情。
王主任曾多次告誡我們,涉法案件不在受理范圍內:“行政單位沒有幹預公檢法辦案的權力。”
可這類求助電話卻不在少數,最常見的是交通事故。
按照交通事故的處理流程,交警部門在進行責任鑒定之後,會對雙方進行調解,如果不能和解,就等待法院的判決。這套流程走下來,少則兩三個月,多則一兩年,躺在醫院的傷者花錢如流水,這種情況下,等不及的傷者傢屬隻能向“市長”求助。
而接到這樣的電話,我們能做的,也隻是向交警隊發一個督辦函,交警隊的回復總是“正在盡力協調肇事方墊付醫藥費”——他們的權限也隻限於此,沒有權力強迫肇事方。
電話裡,常有傷者傢屬要求“市長”把“喪天良”的肇事者抓起來,讓“市長”去給他們要錢。言辭憤憤,或泣不成聲。接到這樣的電話,我隻能建議對方向紅十字會、慈善總會求助,先想辦法籌錢看病,再寬慰一番,僅此而已。
記得有次,接通電話後,我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:“我要殺人。”
那是一個小夥子的聲音。他傢位於我們這裡最偏僻的鄉鎮,那裡現在按正常途徑已經娶不上媳婦瞭,所以適齡男子都是從貴州、雲南“娶”。一個外地媳婦嫁過來後,再接二連三地把傢鄉的姐妹、親戚介紹過來,當然,彩禮也是高得令人瞠目。
電話裡的小夥子為瞭娶媳婦,花瞭20多萬。彩禮給瞭娘傢人,媳婦過來住瞭半年,人就跑瞭。他說之前村裡已經跑瞭好幾個“高價媳婦”,其餘沒跑的,都被傢裡人嚴防死守地看著。
“沒報警嗎?”我知道這事不歸我們管,但還是多問瞭一句。
“報瞭。警察抓瞭介紹人,開始說是詐騙案,可是現在又說證據不足,把人給放瞭。我去找介紹人要錢,他耍賴不給。20多萬啊,就這樣白白沒瞭!我現在錢沒瞭,媳婦也沒瞭,你們政府要是不管的話,我就把介紹人殺瞭,我也不活瞭……”
我不知道怎樣幫助他,隻能勸他珍惜生命,千萬不要沖動之下做出違法的事情。政府管得再寬,也沒辦法給他一個媳婦。
明坑易躲,也有事難辨
有時候,行政專線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,當作談判的砝碼。
我曾接到一個男人的投訴:移動公司施工,在他傢附近挖瞭一個坑,影響到瞭他的正常出行,要求移動公司將這個坑填上——聽起來很合理,所以我們及時給移動公司發瞭交辦件。
可過瞭幾天,這人又打來電話,說移動公司沒有來填坑,讓我們再催一下。
我們打電話詢問移動公司的分管領導,領導說他們早就派人去填坑瞭,但被投訴人阻攔,不許他們填坑,所以無功而返。原來,投訴人想自己填坑,並要求移動公司給他1000元的“填坑費”。移動公司拒絕瞭他,他便通過行政專線繼續給移動公司施壓。
投訴人第三次打電話催促時,我們將移動公司反映的情況和他對質,他支支吾吾起來。接話員告訴他,移動公司承諾會再次去填坑,如果還阻攔的話,行政專線將不會再受理他的投訴。最終,坑還是移動公司自己填上瞭。
有時候覺得隔著電話線也挺好的,當與求助人面對面時,他們裸露的情感會讓本該中立的我們產生偏頗。
有天,一個老大爺推開瞭辦公室的門,他衣著破舊,臉上滿是皺紋,頭發稀疏花白,不知道是怎麼打聽到這裡的。大爺一進門就要下跪,嚇得我們趕緊上前攙扶。
大爺拿起一張照片,上面是一個赤裸的孩子,後背和腿血淋淋的,慘不忍睹。大爺說,這是他的孫子,玩火燒傷瞭,現在在醫院裡搶救。爹媽不負責任,一個跑瞭,一個隻顧自己,他自己負擔不起醫藥費,想讓我們幫幫他。
我們聯系瞭市慈善總會,讓他拿著材料到那裡看看,老人感激地點點頭,步履蹣跚地走瞭。
他走後,我眼前一直晃動著孩子血紅的身體和老人滄桑的面孔,心裡像堵瞭一塊石頭。我從錢包裡拿出200元,追到大廳叫住他,把錢塞到他手裡:“拿著吧,不是什麼大錢……”
回去後,這件事情被王主任知道瞭,他批評瞭我:“首先,老人所說的事情都沒有經過核實,隻有一張照片,很可能是一個騙子;其次,要是開瞭這個頭,以後有困難的人都到這裡來要錢怎麼辦,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就打亂瞭?”
“年輕人啊,不要同情心泛濫。我們有我們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內容,不要超出本分。”
幼兒園裡突然消失的爸爸
能解決群眾的需求和困難,確實讓人愉快,隻是這樣的事並不多。
之前,一個4S店的經理打來電話,說店裡存的水沒用瞭,白白排出去可惜,希望我們能聯系市區環衛處,將這些水送給他們,我從中搭橋,環衛處出動車輛將水抽走,用於澆花澆樹。
還有一次,市裡愛心幼兒園的園長打來電話,說他們那裡有一個小朋友已經半年多沒人接瞭,幼兒園聯系不上傢長,也不敢把孩子丟下不管,無奈之下想到瞭我們。
電話是我接的,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理,就把情況匯報給瞭王主任,他很重視,要園長下午來辦公室將這個事情詳細談一談。
下午上班後,園長過來瞭。兩年前,一個單身爸爸把孩子送到幼兒園“周托”,但半年前,這個爸爸忽然莫名消失,再也沒來接過孩子。直到現在,孩子吃住都在幼兒園裡,衣服也是幼兒園老師捐贈的。
園長說:“孩子吃不瞭多少,幼兒園也負擔得起,關鍵是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啊,孩子生病瞭怎麼辦,他總要找到傢人啊!”
王主任和李主任陪同園長一起,去孩子傢裡、社區、派出所奔波瞭一下午,終於搞清楚事情原委:原來,孩子的父母當初並沒有登記結婚,生瞭孩子後,當媽的拍拍屁股走瞭,當爸的遊手好閑,半年前因為盜竊罪進瞭監獄,孩子就丟在瞭幼兒園。
經過協調,王主任在監獄裡見到瞭孩子的爸爸,希望能通過他找到孩子的媽媽,暫時把孩子管起來。可令人失望的是,孩子媽媽是外地人,和他早就失去瞭聯系。
好在後來我們輾轉找到瞭孩子的大伯,說服他在孩子爸爸坐牢期間暫時看管一下,才算是把這個孩子安頓下來。
事情暫時解決瞭,園長露出瞭笑容,我也難得感受到瞭這份工作的價值。
後記
一年後,我的工作有瞭著落,離開瞭行政專線。
這一年裡,由於經常接觸到負能量,又經常承受無端的指責,所以在鈴聲響起的一剎那,我竟然開始有些害怕,但心裡又不禁揣測,電話另一頭光怪陸離的世間百態裡,又有什麼麻煩事?
什麼都能治,卻又什麼都治不好,這就是“市長熱線”。
本文系網易獨傢約稿,享有獨傢版權授權,任何第三方不得轉載,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。
關於“人間”(the Livings)非虛構寫作平臺的寫作計劃、題目設想、合作意向、費用協商等等,請致信:thelivings@vip.163.com
題圖:VCG
">
市長熱線那頭,沒有市長
南風歌
- 台中商標登記查詢|台中商標登記費用 【品牌達人推薦】如何申請註冊商標台中|註冊商標流程台中?台中事務所商標馬上辦@E@
- 台中註冊商標推薦|台中註冊商標事務所推薦 【註冊商標達人推薦】台中專利商標事務所|台中專利商標事務所推薦?商標申請必看
- 公司註冊商標台中|公司註冊商標推薦台中 【註冊商標達人推薦】商標註冊台中|商標註冊流程台中該找誰呢?申請商標就靠它?@E@
超越智慧財產權事務所|商標申請|台中商標申請|台中商標申請流程|台中商標註冊|台中商標註冊推薦
8FBCA0F78537C490
文章標籤
全站熱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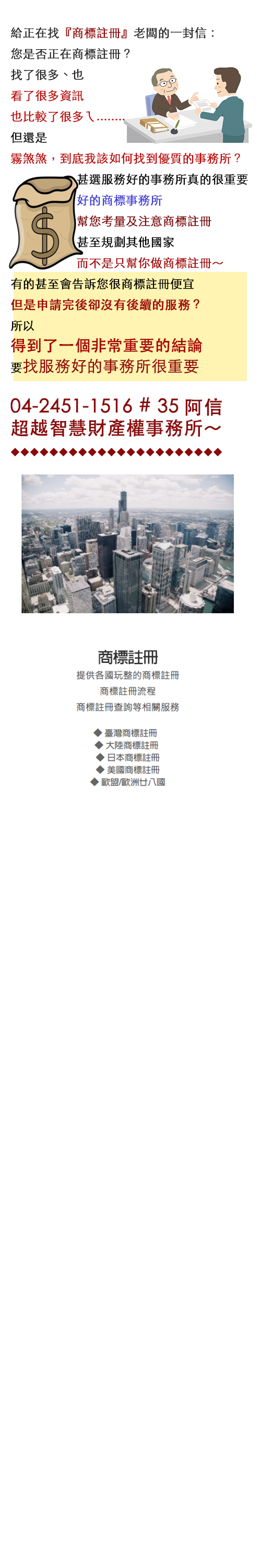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